|
祖屋
在别了四十年的家乡,我发现属于我的家乡消失不见了,或者说,今日的家乡已不是我当年的家乡了。 房屋是完全不同了,不说过去的土砖瓦屋不见了,就是原来的房屋位置、形态都变化了,想必是儿子成人了,结婚生子分家之类的事情,一个家裂变为两三个家,随着老一辈人离世,房屋自然破败,荒芜,消失。房屋变化了,道路跟着变化,新建了房屋也就新修一条道路;老屋荒废了,道路也会因缺少人走而杂草丛生,渐渐看不到路了。 我家祖屋,变卖给了乡亲,若干年以后,乡亲搬到了别处,此宅基地又回到了我侄儿手里,侄儿拔除老屋重新布局,新屋完全是新式结构,涣然一新。印象中,我家邻近的人家有四五家,如今只剩侄儿一家了,当年的晒谷坪、天井均不见了,屋前的牛栏屋、小池塘、一排约五六棵高大的杨树、柳树,都无从寻觅,我要努力回忆,才能依稀找到某些风物的原址,但也不肯定。只有我们曾经玩水的大池塘还在,感觉比当年小了一号。 有时候我在想,家乡的风物应该不变才好,那么,我们这些离开家乡的游子,就能够看到自己熟悉的生活,会产生一种亲近的感情。岁月悠悠,几十年后再度踏上儿时的土地,该是怎样的感慨?“千里草,萋萋尽处遥山小。 遥山小,行人远似,此山多少? 天若有情天亦老,此情说便说不了。” 说不了呀! 倘若家乡的风物真的一成不变,又将惊呼家乡的原始落后了。当年离开家乡时,正是物质生活贫乏时期,家家户户外墙上书有大幅政治标语。醇厚的农民,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悠哉悠哉。相反,家乡真是我儿时的样子,则与当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相去甚远,又该做何感慨了? 侄儿的屋,两层小楼,红砖的墙体,白色瓷砖的外墙,乡村比较常见的结构,屋里的生活设施,也与城里差别不大,在这里居住,很是适应,并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。 侄儿比我小三岁,是我儿时的玩伴,他说,小叔你小时候真的很调皮,你妈追你不到,你在这坪里满场飞。我实际上已经不记得自己的样子,经他一说,我没有置疑,那场面当然只属于他们,我作为当事人自然看不到自己了。但是,我的眼前却出现了当年的这个场面。我对侄儿笑了笑,我知道这是一种满意的表达,谢谢他给了我一幅美丽的画面。 在房屋周边走走,思绪时常在穿越,儿时与母亲生活的气息,仿佛就在身边,此时此地,或者彼时彼地。四十年的时差,造成了一种奇异的感觉,我的眼前是当年的母子,而当年的母亲却在看今天的我。近在眼前,却遥不可及。 坐在侄儿的房屋里,感觉我的模样像极了父亲;我感觉似乎是父亲坐在了这里,他的侄儿(我的堂兄)在陪着叔叔聊天。不知道在我的侄儿眼里,是否也有这种幻像。两代人,居然有着某些相似的场景,仿佛是生活的周而复始。 夜晚,照例是黑色的主角,明月照样高高的在天上挂着,只不过,当年唱着“月亮光光,挂在树上”的母亲,已经到了天上,望着这个曾经笑过哭过的地方,想着而今的人已经极少想起她了。偶尔也有萤火虫闪现,它或许跟我一样,是当年同类的儿孙,已不是我儿时被我追逐的那些个小精灵了。 儿时的夜晚是有些恐惧的,恐惧着夜,恐惧着那些不存在的人,或者鬼故事里的幻想。如今,感觉自己的父母亲人就在身边,就像是陪伴我散步一样,可以什么都不说,但却很温暖。我躺在床上,父母亲躺在山坳上,近在咫尺,已经没有了阴阳相隔的感觉。很是平静。想起儿时的恐惧,竟忘了那时是怕些什么呢? 与儿时不同的地方也有,没有鸡鸣,没有狗叫。侄儿说了,大家不养狗了,一个是不需要狗来护家了,没人偷东西了;二个是狗咬人划不来。没有鸡鸣是凌晨的事,儿时司晨靠鸡,如今却冷冷清清,但是醒来不方便问,过了这个点又忘了问了。 我早早就醒来,已经不用鸡鸣了。天刚蒙蒙亮,我背起摄影包,抓起手电,轻声外出了。在侄儿新屋的周遭,我寻着合适的角度,等候太阳出来。太阳把天空云的颜色染上了红的黄的紫的,侄儿新屋的轮廓清晰可见,屋前池塘的水面渐渐也染上了细碎的红色黄的紫色。我不断按下快门,不断换着位置。美了,我的家乡,我的祖屋之处。我只是不解,儿时日日在这里玩耍,从来没有觉得美,没有想过这是美。 祖屋之处的一夜,是一种过往与现实的混合,是记忆生活的交织与叠加,仿佛摄影手法的多重曝光,让人忘却了时空在流动,也让人逾越了阴阳。
老 井
在儿时的老屋处,总是忍不住要想起往事来。跟城里的妻儿说起四十年前的乡村生活,他们很是新鲜,我也很有意味。其中,关于半夜担水的故事,引起了寻找老井的冲动。找了砍刀,铁锹,披荆斩棘,一路汗水,终于打通了到老井的路,见到了久违的老井。 几次回家乡,总是在物是人非中找寻。 老井,几乎被我忽略。如今的农家,或装有自来水管道,或房前屋后打了深井,一个杠杆压一压,井水汩汩流淌,再也不见水桶与扁担,蓄水的缸也自然没了。这些物件的消失,我记忆中的担水活动,也就成了没有引线的炮仗,无法燃着与炸开火花。 按照生存法则,水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。每天,人们都要去井里担水,灌满自家的水缸。有些东西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似的,而且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,倒没有觉到它的珍贵,就像空气,就像水。但是,一旦遇到"万一",饮水水源变得稀缺,水也变得"物以稀为贵"了,老井才显示自己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了。这一点,我是经历过的。 那年干旱,井里缺水。 那时候,还是靠天吃饭的。可是,老天不是洪涝就是干旱。这不,大热的天,本来就口里干得冒烟,却没有水来解渴,让人心发慌。 心发慌的人们在到处找水。我也去找水了,就近的几个水井都见了底,从来没有感觉水是如此的珍贵。好在我家只有母子二人,用水节约点,一担水足以用一天。 尽管这样,水仍然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。白天,在井边等候挑水的人要排队。都是眼巴巴地等着那清流能够喷涌而出。但那只是一种愿望。实际上,水好像都枯竭了一样,根本看不到水涌出来的样子。妈妈说,我们只有等,等到晚上才行。 没有水的日子里,我也不敢放肆疯,担心玩累了,口干了,却没有水来解渴。妈妈则弄了一些甘草、绿豆稀饭、苦瓜什么的来清凉,缓解口渴。天上的日头白花花地照着,知了在枯燥地聒噪着,世界好像都要起火了一样。 每天晚上,我总是在迷迷糊糊中被妈妈弄醒。然后,不用分说,妈妈挑起水桶就出门,让我打着电筒走在前面。万籁俱静的夜晚,弯弯的月亮象镰刀一样,在天空悬着。我没睡醒似的,迷迷糊糊就听从妈妈的话语,朝着水井的地方走着。沿着窄窄的池塘塘堤,我低头看路专心走,怕看那黑隐隐的山,我不知道那里暗暗的丛林中藏有什么。妈妈让我用竹竿在前面探路、赶蛇,偶尔有受惊的青蛙跳到塘中,“咚”地溅起水花,也能吓我一跳。到了宽敞处,妈妈便牵着我并排走,这时我便什么也不怕了。 经过大半夜的等候,原先干枯的水井有了些水,而且,那水看上去并不象平时那样清澈,有些混浊。因为井里的水很浅,妈妈必须下到井底,才能取到水。妈妈是有些胖的。她就踏着井边的石块,慢慢下到井底,然后用竹勺轻轻地舀,半桶,便举起,让我在上面使劲提。我人小力气小,只能提半桶,然后又用另半桶倒成一桶,最后的一桶,妈妈便在井上用扁担勾了上来。 当妈妈在井里舀水时,我独自在井的上面依然害怕,心怦怦地跳,总忍不住喊一声“妈妈”,“妈妈在,崽。”妈妈的声音是发颤的。 当我们担着水回到家插上门,重新上床后,妈妈便紧紧搂住我,用手从我的头上抚摸到背上…… 村里隔上一段时间就会把水井清理一下,把水舀干,清除井底的树枝树叶等杂物,在井壁洒上白石灰消毒。夏天的时候,水井的水很清凉,我们会在井里舀水喝,或洗一些果子吃。但是,大人教诲了,对井水是不可造次的。因而,在我们孩子心目中,老井充满神圣的感觉。 社会的发展,科技的进步,终究让一些东西被取代,消失。水井,当年人们如此依赖,如此神圣的事情,渐渐地,因担水的人不再,通往水井的道路长满了杂草灌木,水井也被竹木遮住,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她像一个历经了风雨沧桑的老人,归隐于竹木之中。 这天,经过一个小时的披荆斩棘,打通了从菜园到水井的道路。终于,久违的太阳光,照射在到了水井上面,水面上漂浮着一层绿藻,拨开它,可以看到倒影着绿叶的影子。朦胧中,我似乎看见一个少年,跟随挑着水桶的母亲,来担水了。 我发觉,我整理出来的不仅仅是一条荆棘丛生中的道路,而是一段童年生活的记忆;我们打通的好似是一条时空隧道,让我穿越了四十年,看到了当年熟悉的老井。 再见老井,仿佛见到了一位久别四十年的友人,她安静地看着我们,不悲不喜。反倒是我们,虽有一丝久别重逢的喜悦,但也心存打搅的内疚。老井,她已经不合时宜,她已经被人忘却,但是,她一直是我心中一道难以抹去的风景,一段相互见证历史的情愫。
田 埂
阳光很好,照在春天的田野上,也照着老屋前晒太阳的我们。 我望着屋前开阔的田垄,想像着四十年前,我在家门口望着田垄里出工务农的母亲,盼着她回家做饭吃的情景。心中顿生一种想法,到田埂上去走一走。 油菜花已经结籽,如果摄影,该是萌萌的一片;紫云英,我们小时候叫草籽花,倒是开得正旺,营造出一隅紫色的田野;有些田显得光秃秃的,仔细一看,有些小秧苗已经冒芽了,过不了几天,就会长出一层嫩绿;田垄中间是一条小河,小河边自然生长着一些小树,郁郁葱葱的;远远的看见小河边有几只白鹭,或觅食或飞起来。想接近看个究竟,白鹭们却一直保持距离,见人就飞。 春天的小草绿油油的。我时常看着脚下的米粒草发呆,那嫩绿的叶子,以及像米粒大小的白色小花,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呀。时光倒回四十年,我会视若珍宝,把她带回家。妈妈会夸我能干,我便会更加得意。不过,那是儿时的我。 上学后的我,能帮母亲做不少事情,扯猪草就是一件。每当放学,我放下书包,拧起小竹篮,手抓小镰刀,去垄间田埂上,村前小河边,或是山坳上的茶园,到处去扯草喂猪。到傍晚时,把扯来的一篮猪草到塘边,洗去泥巴,给母亲剁碎后煮成猪食喂猪。 春天的草,扯完又生,我们很快就扯满了一竹篮,于是几个小伙伴就会凑到一起玩。有时,会在长满草籽花的田里玩投掷游戏,并且有点小刺激。我们用两把小镰刀交叉插进泥土里,然后在距离镰刀十步远的地方划线,用另外一把镰刀作为投掷物,去击中并打倒十步以外的交叉在地的镰刀,即可获胜。击打之前, 每个人可在十步线上放一小撮扯来的嫩草作注,如果谁能击中目标镰刀,即可把地上所有的作注的草收进自己的竹篮。 脚下的道路与儿时有些差异,也有个别田埂似乎还是原来的模样,能够唤起我的记忆。其中一个小池塘,旁边就是我家的自留地,母亲带我在这里摘黄瓜、豆角、茄子、苦瓜什么的。黄瓜豆角摘下即可生吃。如今,这地里没有种菜,而是混淆在一片农田之中了。 田埂还是窄窄的,上面的泥土时而干时而湿软。小孙女在箭步如飞,我担心她会不小心掉进田里。其实,我小时候不也是这样吗?如今的我,则很小心,挑拣着路走。这种姿势,搁在四十年前,一副非劳动人民的模样,或者拈轻怕重的丑恶,一定会遭人鄙视的。这么想着,会四下张望,有没有人看见。田垄里不见劳作的人群,不知山坳上是否有人看见。当然,如果当时的我们,是纯粹的吃国家粮的城里人,或者不懂打赤脚的干部,以我儿时的眼光来看,一定是有一些羡慕,或者嫉妒的。 我走到了一泓大池塘边上,还有一丛树木。这里曾经住着陈姓的两家人,有我儿时的玩伴,如今已经无人居住了。这令我想起十岁那年的一场大水了。那场大水浩浩荡荡排山倒海,冲倒了田垄里所有的土砖房,家乡熟悉的风物,发生了彻底的改变,只有房前屋后的树木,标志着这里曾经住着人家。我们凭着这片树木所在的位置,判断着这里应该是某某家。 走在家乡的田埂上,那些远去的岁月又一一浮现出来,欢笑的,悲催的,都有;有的人已经不在了,有的人不知道在还是不在,如果在,如今该是什么模样? 抬头看看天空,看看远方熟悉的山坳,我终于明白,这一方水土,无论她变或者不变,都是我不变的眷恋;那些远去的人,与自己生命有过交集的人,四十年的风雨洗礼,无论他(她)在或者不在,都会让我感到亲切。 这难道就是乡愁? 这或许就是岁月在我身上老去? 乡村的春风微微的,泥土气息清清的,家乡久违的田垄,依然如故,更加清新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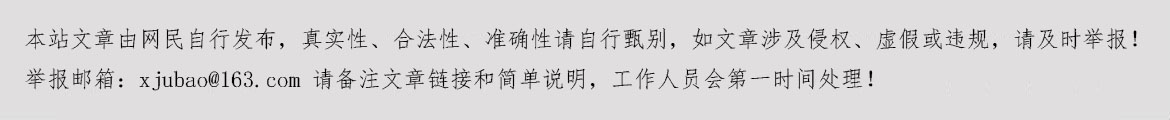
|